意象 心灵图画的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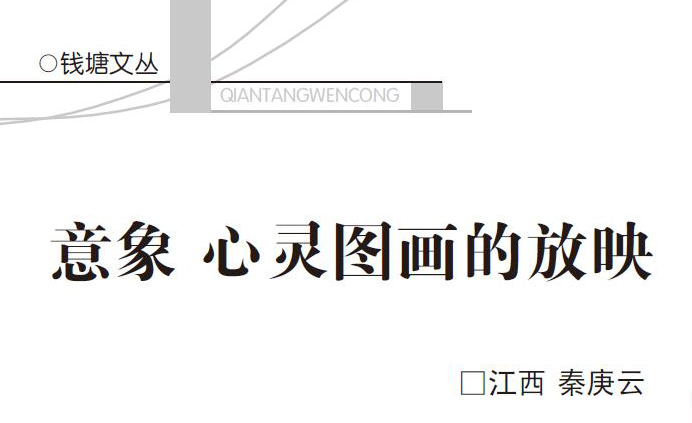
歌词的形象有三种:
一种叫“自象”。这是抒情主人公的直接形象,也叫自我形象,它有最强烈、最直接的直抒可感性,例如《我是一个兵》、《咱们工人有力量》等。
另一种是近似白描式的形象。它直白、坦露,用作者的视觉、听觉去直接诉诸于听众的视觉,叫“视象”,例如《桃花盛开的地方》《小芳》等。
第三种是通过移情、通感、象征等手法酿制的感官印象。它是玄妙的物象、情感的霓裳、心灵的图画,这就是“意象”——意识之象,变形变异之象。比如“黄河入海流”是“视象”,“黄河之水天上来”是“意象”,而《保卫黄河》用的就是“意象群”了。
艾青把形象和意象分开论述,他认为“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他告诉我们两点:
①意象是感官的印象,是感觉经验的语言表现;
②意象是感情的力量对万事万物进行全面改造后的具象,是主观的“意中之象”,是变形的“意化为象”。
让艺术形象与实体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意象就上升为高级形象。
同是写太阳,涅克拉索夫这样描写:“圆圆的太阳,/迟钝地/好像圭枭的一只黄眼睛,/冷淡地从天上俯视。”(《严寒·通红的鼻子》)
聂鲁达这样描写:“在我头上升起了/圆溜溜/热烘烘/孤零零的/太阳——/就像一头/披着亮闪闪的/红鬃的/狮子/在场子上团团转。”(《太阳的颂歌》)
艾青又这样描写:“午时的太阳,是中了酒毒的眼,/放射着混沌的愤怒/和混沌的悲哀。”(《马赛》)
——从变形的程度与特征,我们区分开了意象与视象。
中国诗词的意象思维方式是最早的。(直到20世纪初叶,才出现欧美青年诗人组成的意象派。)汉语的诗词意象又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汉语是“孤立语”,意象不需要通过任何语法联系,可以直接一个接一个“蒙太奇”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直接感触到事物本身,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象;如元人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又如叶佳修的《外婆的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而英语是“屈折语”,不能使意象以彼此独立的形式出现,日语是“粘着语”,助词的必需与语尾的变化,也妨碍它取得复合意象(也叫组合意象、意象叠加)。
汉语意象有凝炼性、言简意赅,将细节凝缩于一个观点之中;汉语意象又有丰富性,组合巧妙,构成了一幅(一组)既有统一情绪,而又意蕴丰富的画面(组画)。
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化了唐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一个又一个的意象跳跃与连接,都统一指向情与事的中心——“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在这首词中,意象的运用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准确鲜明生动地描写事物的各个方面,而是为了表现作者在引发自己感动的那一瞬间的感觉,而那瞬间攫住作者心灵的印象——是一道光影(渔光)、一个图象(枫桥、风霜)、一缕声响(钟声、乌啼、涛声)等意象,组合成秋夜景色的典型意象群,有效地传达出词人周围的环境以及心头引起的反应,构成了一种人生旅途和心路历程的情愁氛围。一旦这种氛围被完成之后,词人的一声探问,甩笔引出了对于此词最为重要的“旧船票”的意象。这一意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见物思人”,更能映衬出“他”的旅途寂寞和那段难以割舍的旧情愁绪。如果缺乏了这个主导意象,它就失去了灵魂;如果没有前面秋夜意象群的映衬与烘托,这个主导意象也就显不出它的情韵悠远、意味深长了。《涛声依旧》让我们看到了意象的凝炼性与丰富性的完美结合:删繁就简,斫尽旁枝杂叶,却又意丰蕴厚而笔饱墨酣。
唐人李商隐的名篇《乐游原》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叹老之意极矣,然只说夕阳,并不说自己,所以为妙”。
18世纪苏格兰诗人麦克浮生的《奥森诗篇》有这么一节:“奥森刚才不曾听见一个声音吗?/那就是已往岁月的声音。/往时的记忆往往像落日一样/来到我的灵魂里。”
19世纪德国诗人海涅赞咏的两句诗:“太阳纵然还是无限美丽/最后它总是西沉”。而李商隐的“夕阳”意象比海涅和麦克浮生这些西方诗人的“落日”意象要高明得多。他们总是用那些亘古如斯比喻来作人生道理的阐述,而李商隐只是描写他亲眼所见,却又很自然地蕴含着某种人生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李商隐的自然、含蓄、生动,确在海涅们之上。
乔羽反李商隐原意所作《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短短几句,一扫迟暮之感,四个排比的意象,将夕阳染得“温馨又从容”。是感情的色彩让夕阳更“红火”,让人生更美丽。意象的凝炼性与丰富性,在老辣旷达的词家笔下可窥一斑,这是“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诗歌与语言已经发展完全,最平庸的作家也知道如何造句,如何换韵,如何处理一个结局。这时使艺术低落的乃是思想感情的薄弱。”
意象派庞德说:“‘意象’是在刹那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的情结……正是这种情结的瞬间出现,才给人以摆脱时间局限与空间局限的感觉,才给人以突然成长壮大的感觉。”思想感情与创造意象,思想观念与创新意象,是特别密切相关的。
许多短词,它的意象是单个的,它的手法也是较单一的,而大量的歌词都由丰富的意象组成,意象的跳跃、并置、组合、叠加手法以及比喻、拟人、移情等多种修辞的综合运用,让我们在歌词写作中如鱼得水,特别是象征手法,使汉语歌词的意象表现超越了个人性与暂时性,从而获得了普遍性与永久性的效果——象征,中国人集体的潜意识。
顺附笔者之《花朝节到了》(刘安华曲、李涵演唱),供青年朋友参考之——
花朝节到了
花信风送来了春天的喜报,
花山女唱起了争春的歌谣,
畲山戴上了花冠,
畲家戴上了花帽,
畲乡流出的花溪水,
那个叮叮咚咚蹦蹦跳跳哎,
跃下了山崖,绕过了山腰,走过青青草,
走成一片花的春潮。
老阿公捧出了二月的花苞,
老阿婆领来了春天的花轿,
阿妹披戴着花红,
阿哥点燃了花炮,
畲乡迎亲的花灯调,
那个咚咚锵锵热热闹闹哎,
叫是百鸟叫,笑是百花笑,俏是儿女俏,
汇成一片春的花潮。
哩罗哩,哩罗哩!
花朝节到了,花朝节到了——
花魁来了,花王来了,花神来了,花仙来了!
花山荡漾着春天的祈祷, 花海扬起了畲家的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