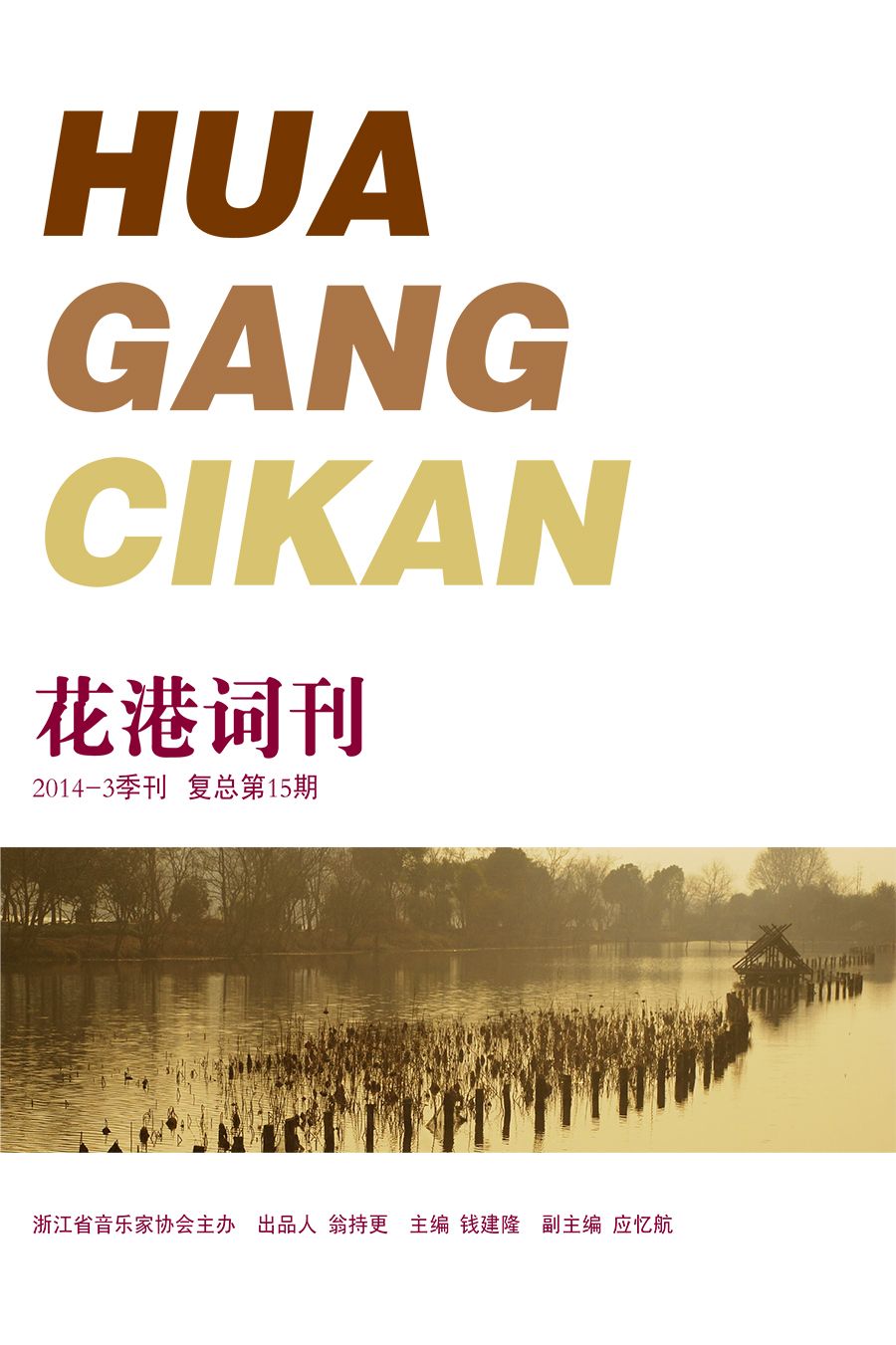私人订制的好歌

日前,历时三个月热播的《中国好歌曲》节目在央视三套降下帷幕,青年唱作人霍尊凭借与费玉清合唱的的《卷珠帘》,在《中国好歌曲》总决赛中一举夺得“年度中国好歌曲”的桂冠。这台由央视三套与灿星制作团队联手推出的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给中国原创歌曲创作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
什么是好歌曲,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何况冠名为《中国好歌曲》,按惯例也该官方说了算,因为它要代表主旋律。可你一看它的参赛歌曲的歌名,就知道是非主旋律的作品。比如:霍尊的《卷珠帘》、周三的《一个歌手的情书》、谢帝的《明天不上班》、王晓天的《再见吧,喵小姐》、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马上又的《她》、张岭的《喝酒BLues》、柳重言的《空白的缘份》、乌拉多恩的《鸟人》、灰子的《灰鸟》、苏珮卿的《格格不入》、邱振哲的《我不需要》、铃凯的《一个人》、老钱的《今天我疯了》等等。可这些歌曲却得到不同人群的喜爱和关注。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大陆原创歌曲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的回归。《中国好歌曲》节目对于我们正在从事文化管理和歌曲创作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思考和启示呢?笔者以为:
一、大陆歌曲创作的命题形式已经由官方订制为主开始转向私人订制、自我订制为主。创作不仅仅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个人爱好的需要和谋生的需要。由于体制的原因,以往我们许多发表和播出的歌曲都是由国家订制、地方订制、组织订制、企业订制。像国歌、奥运会会歌、市歌、厂歌、校歌、主题歌等等。而《中国好歌曲》节目上的参赛歌曲几乎全是私人订制、自我订制的。他们为自己、为亲人、为所爱的人、为所关注的事所写,题材面虽小了,但创作从心出发,真情度高了,感染力更强了。比如王矜霖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唱给未来的岳母,赵照的《当你老了》唱给母亲和自己,沙洲的《挖蛤蜊》唱出挖蛤蜊时的开心,赵雷的《画》唱出自己的寂寞生活与梦想,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写给妻子,王晓天的《再见吧,喵小姐》写给流浪猫和流浪的自己,苏丹的《寂静森林》唱给身心受到摧残的狗熊,等等。这些都与宏大叙事、地方发展、企业创收无关,但却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情感生活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二、大陆歌曲创作已经从有限精英的“少数玩”的艺术发展到不分社会阶层的“大家玩”的艺术。过去从事歌曲创作的人,主要是来自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文化馆站的专业、半专业人士。 而现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的唱作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人数众多。有著名音乐制作人、作曲家、音乐编辑、文学博士,也有公交车司机、自由职业者、街头艺人、高校师生、公司职员等,呈现出大家一起“玩音乐”的喜人景象。“大家玩”比“少数玩”要热闹、有生气,有道是“水清则无鱼”。当然,“大家玩”由于门槛底、应者众,而显得庞杂无序,不那么纯粹和经典。但这只是歌曲艺术由一个高峰到另一高峰的必然过渡,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会有上上品出现的。
三、大陆歌曲创作已经从“官场”“会场”模式为主转向“市场”模式为主。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改作风反“四风”,各种音乐比赛、文艺晚会的数量和规模大大减小,官方订制的歌曲减少,走“官场”、 走“会场”,已不再是大陆歌曲面市的主渠道,走“市场”开始成为大陆音乐人的首选。而《中国好歌曲》的运营模式,提升了市场因素。现场观众、51个媒体人组成的乐评团和导师们一起鉴歌选歌,将他们的现场观感通过掌声、分数和氛围反馈给导师及制作团队,使其各自制作的原创大碟未卖先“红”(被人知晓)、 未卖先“传”(流传)。用参赛者的说法是“一场超大型的现场卡拉OK”,用导师刘欢的话说:“是一个唱片首发展示会”。像霍尊那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卷珠帘》,才经过《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已经荣登2014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了。
四、大陆歌曲的受众方向开始由“大众化”走向“小众化”。既然订制是私人订制、自我订制为主,创作是大家各自“玩”,销路是市场说了算,那么,“小众化”的趋势就不可逆转。笔者曾在《中国现代歌词走过百年的思考》一文中提到“百年历程是一个不断走向大众又不断回归自我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也是艺术风格从单一性走向多样化的过程”。现在的中国大陆歌曲正处于回归自我多元发展的阶段。不少《中国好歌曲》节目上的被选歌曲,从歌词中提出的理念、想法和曲调风格上看,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但仍然拥有相对固定的共鸣者和存在价值。比如谢帝的《明天不上班》和苏珮卿的《格格不入》。歌曲《明天不上班》原名为《老子明天不上班》,延续了《我的地盘我作主》的霸气和直白。是对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的一种不满宣泄,同时也传递出工作与兴趣爱好之间的矛盾冲突。歌曲《格格不入》,听歌名就不打算让多数人接受,但你细看歌词本身,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的矛盾纠结,唱出了“哪里才是我的天,怎麽才能有个好眠;难以拿捏的进退,格格不入的感觉”的人生感叹,仍有不少人喜欢。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和文明民主的进步。
五、大陆歌曲的好与坏,不再只是官方说了算、专家说了算,它要接受市场和受众的检验。判断的标准也从单一的政治与艺术相统一,走向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阳光大道。过去比赛评奖大都是先由专家评,再由领导作最后敲定,专家有好恶、领导有亲疏,彼此平衡的结果:评出的歌曲要么是艺术个性不鲜明、要么是感情不浓烈、要么是内容假大空。《中国好歌曲》节目上演唱的歌虽没有大题材、大制作,但却通过每个创作个体直接的人生体验和艺术追求,为我们勾画出鲜明独特的芸芸众生相。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不易与不朽。这才是鲜活的歌曲艺术。同时,《中国好歌曲》也提示我们,歌曲好坏的判断标准,不光靠“大我”、“小我”的题材区别以及某些技巧技术的运用是否先进时尚,关键是走心了没有,让你感动了没有,说出我们心里话没有?
六、在《中国好歌曲》节目中,也涌现出许多值得人们记住的好歌词,这些来自唱作人的真实内心新鲜而多彩的歌词,必将使当今词坛普遍受益。像霍尊的《卷珠帘》:“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画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淌,千家文都泛黄,夜静谧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徘徊,相思蔓上心扉。她眷恋,梨花泪,静画红妆等谁归?空留伊人徐徐憔悴”, 赵雷的《画》:“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苏珮卿的《格格不入》:“也不方,也不圆,我们都留一点空间,欣赏对方圆缺。也不红,也不黑,我们拥抱彼此状态,融合出新色彩,困在输赢是非纷扰不清的世界,伸展双臂才发现,还有更高的天”,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亲手摸过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你呀你,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这颗心就稀巴烂,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铃凯的《一个人》:“一个人看着浪漫午夜场,剧情会不会太夸张?双人床我已睡得有点烦,翻个身翻出了旧账。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当初最完美的典范,有时感觉不过是种假象”。上述歌词或语言新颖、或情感真挚、或意境深邃、或兼而有之,为我们的歌曲创作提供了好的范本。
七、《中国好歌曲》节目是开端不是结束,是暖场而非救场。真正的音乐繁荣有待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创新。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玩”音乐是必须有点政治头脑的,因为歌曲与政治结合的太紧。一是官方的参与度高,有关部门大多通过征歌和大赛来把控文艺的政治导向。二是歌曲的政治功用性强,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三是上述原因造成艺术风格趋同性明显,凡能登上主流舞台的歌曲作品,常常成为创作者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由此笔者想到著名画家吴冠中的那张被拍出2750万的巨幅水墨画《鹦鹉天堂》,至今令人回味无穷,它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绘画本身,你懂的。四是现有的传播舞台有限,文化市场、流通渠道均不发达。虽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也是星途漫漫。因此,有唱作人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被导师选中时,连呼多个“不可思议”,弄得现场导师和观众有点懵。笔者当时心中一惊:该不是现代版的“范进中举”吧?笔者事后分析他的“不可思议”,大概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无业歌手能登上官方舞台不可思议。二是非主流歌曲能登上主流舞台不可思议。三是无名唱作人被有名唱作人肯定不可思议。四是小众化东西被大众化世界接受不可思议。
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我们的音乐梦想也和其它梦想一样,“不可思议”。让唱作人尽情尽兴地自由创作,让受众们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听的歌,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