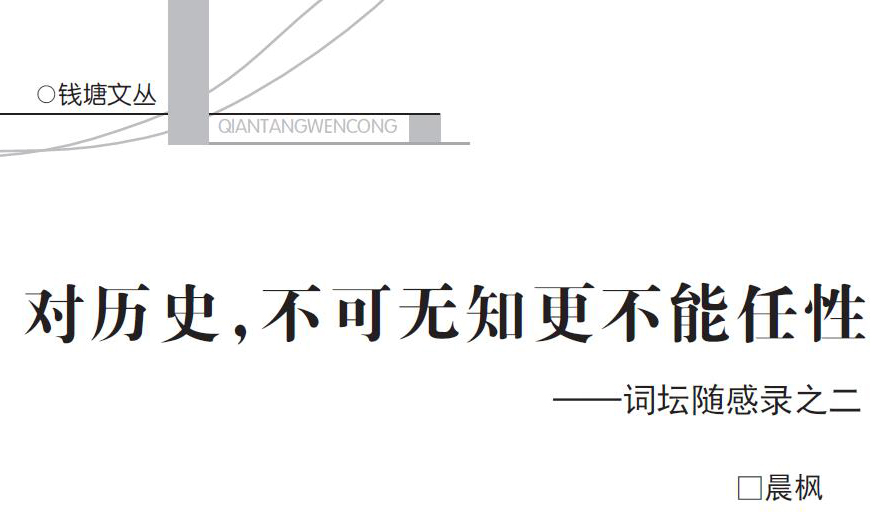歌词就是音乐文学吗?

记者:晨枫老师,受《花港词刊》委托对您进行采访。作为歌词作家,您创作了《火箭兵的梦》等一批佳作,同时在音乐文学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倾注满腔心血写下大量观点鲜明、见识独到的文章。前不久再版的《中国当代歌词发展史》一书,音乐界反响强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当代歌词发展历史的专著。但不过今天采访主题,是想请您谈谈有关音乐文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看法。
晨枫:好的。
记者:在歌词界,有一种将歌词与音乐文学相互混用的现象。您认为歌词与音乐文学是同一个概念吗?
晨枫: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今的歌词界的确带有普遍性,我以为如果能加以认真探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理论上廓清有关歌词艺术的一些基本概念,还会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歌词艺术的文化含量,开拓我们的创作视野,以便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音乐文学领域里自由驰骋,为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施展才华,多出佳作。
其实,将歌词与音乐文学相互混用的情况,在当今的一些歌词刊物上时常可以看到。比如,有的分明只是专门评析歌词作品的文章,却常被称为音乐文学评论;有的出版的分明是多人的歌词作品选集,却冠名为音乐文学作品集;有的将只是单一从事歌词创作的作家称为音乐文学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证。
然而事实上,音乐文学与歌词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音乐文学实质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指所有以语言为表现工具,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手段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传递人们的思想情感,并且能够在与音乐结合之后,以歌唱的方式诉诸于人们的听觉。既然如此,音乐文学当然首先应当包括歌词,因为歌词与音乐结合成为歌曲之后,其所产生的广泛受众面与巨大影响力,是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比拟的,这也就使得歌词成为了音乐文学的主力军。然而,主力军并不意味着全部,至少在我国近现代的艺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歌词之外,例如歌剧剧本、戏曲文本中的剧词以及弹词、鼓词、杂曲、牌子曲等说唱艺术的唱词,因为都是与音乐结合后成为演唱的声乐作品,因而也都属于音乐文学的范畴。
对此,生前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讲授《音乐文学概论》的庄捃华先生,在她最终未能全部完成的该书“导言”里,就以“音乐文学的含义”、“音乐文学的范畴”与“音乐文学学科的确立”等为题,提出了自己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同的见地。作者在该书的“上篇·歌词”一章里,就歌词的产生、歌与诗、歌词的特性,素材、题材与主题、形象、节奏、音韵以及语言修辞等,均一一进行了详尽的解析与阐述,传达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让人遗憾的是,该书本应辑入的“下篇·歌剧”一章还未及成文,作者就不幸辞世。但仅仅这本专著的构架就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在作者看来,音乐文学除了歌词之外,至少还有戏剧与说唱艺术中的可唱的文学部分。这样看来,歌词不能等同于音乐文学,更无法替代音乐文学,只能是音乐文学的主要品种。
记者:在我国,音乐文学这一概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了今天,音乐文学的内涵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晨枫: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我国的音乐文学可以说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因为从诗经到楚辞,从汉魏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等等,我国的韵文文学的发展,始终未曾离开过音乐,所以,都应当属于音乐文学的范畴。这其中不仅有大量同音乐曲牌相联姻的较为短小的韵文作品,更有像元曲这样包含着元杂剧与散曲内容的戏剧品种,足见音乐文学概念的宽泛。正是基于此,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便出现了一本专著《中国音乐文学史》。
该书作者朱谦之,早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是一位在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以及中外文化关系等多种领域皆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在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教授。1934年,朱先生在厦门大学时,就开设了《中国音乐文学史》课程。1935年,该课程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反响颇佳。翌年,经过日本学者横利一川翻译,该书得以在日本出版发行。而进入改革开放后的1989年和2006年,该书又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先后出版。这种在国内外的反复再版的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见证了这本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本由学者撰写的音乐文学理论研究专著和其开山之作所具有的珍贵学术价值。
在这本书里,作者通过“音乐与文学”、“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关系”、“论诗乐”、“论楚声”、“论乐府”、“唐代诗歌”、“宋代歌词”和“论剧曲”等八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历史。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于音乐文学概念的定位与理解,包括了我国几千年间各个历史朝代里出现的所有与音乐相关的韵文。朱先生也因此认为,“中国文学的进化,彻始彻终都是和音乐不相离的,所以有一种新音乐发生,就有一种新文学发生……汉魏之乐府,唐不能歌而歌诗;唐之诗,宋不能歌而歌词;宋之词,元不能歌而歌曲”。足见音乐与文学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不仅始终是相互伴随、不曾分割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往往是在音乐的推动下发展的,足见,音乐文学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而又厚重的概念。
在封建体制解体、尤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随着时代的迅疾变迁与社会生活内容的不断变化与小说、散文、话剧、随笔等等文体的兴起,特别是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白话诗的出现,使得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同音乐联系紧密的文学格局,发生了裂变——口语化的诗歌摆脱了以往格律、平仄枷锁的羁绊,更加朝着满足人们对于白话文阅读需求的方向发展,也使以往与音乐最为亲近的诗歌也基本上离开了音乐,就这样,诗歌与歌词的一源二流的发展趋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以沈心工、李叔同为代表的“学堂乐歌”的先辈们,给欧、美、日本的音乐旋律填上汉语歌词,在中小学课堂上开设“乐歌”课;另一方面以萧友梅、赵元任、黄自等作曲家们也开始为现代诗人的诗歌谱曲,于是,我国近现代歌曲的历史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专门为与音乐融合成歌曲的文本歌词,也就水到渠成地产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1935年朱谦之先生首先提出音乐文学这个概念之外,从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我国近现代歌词产生起,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光里,虽然公木先生将歌词称为歌诗,但在人们的音乐文化生活中,歌词这个文体同音乐文学却一直未曾明确发生过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说歌词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同时讲到音乐文学,包括1980年中国近现代第一份歌词刊物《词刊》的“创刊词”、1981年2月开始筹备的“北京歌词研究会”以及同年11月在株洲召开的“全国歌词创作座谈会”这几个重要事件在内。事情的变化则始于1985年5月15日,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的正式成立,才使得音乐文学这面大旗终于被歌词作家们高高举起。对于我国近现代歌词艺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发展中的里程碑。而在此同时,沈阳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则先后在作曲系设置了音乐文学专业,同样是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
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些院校对于音乐文学专业的阐释是,音乐文学是集音乐、文学、戏剧于一身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因为必须受制于音乐的制约,俗称为“带响”的文学。其中包括歌词、歌剧剧本、电视音乐剧、音乐艺术片的文学脚本等等。不难看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音乐传播媒体因触电而发生的多样化与声像一体化等等,使得音乐文学的内涵不断有所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些与当今音乐传媒有关的文体。但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音乐文学的概念并不仅仅只是涵盖歌词一种。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认为音乐文学指的就是歌词、并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呢?
晨枫: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歌词被谱曲成为歌曲之后,一俟被演唱、被传播,其所拥有的受众面之广泛与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之巨大,是其它任何艺术品种无法比拟的,其中也包括音乐文学中的其它姊妹门类,如歌剧剧本、音乐剧剧本、戏曲文本、电视音乐剧、电视音乐艺术片以及其它各地区不同民族说唱艺术的文本在内。正是歌曲这种自身的强势,让许多人(包括许多作者)只知全身心地经营歌词,而很少或者根本不去深究音乐文学是否还有其它姊妹艺术。因而,如果偶尔提及音乐文学,便很容易同歌词划上等号。
其二,由于我们歌词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力量的薄弱与工作的滞后,包括各级音乐文学学会自诞生以来,除了对于歌词本身的研究与评论还略有收获之外,对于音乐文学的其它艺术品种,无论是在人员的吸纳上、还是在对创作的关注上,几乎长期都处于缺位状态,至于研究也就更加难以谈到了。这种音乐文学学会实际等同于歌词学会的真切现实,使得以歌词艺术替代音乐文学的现象似乎成了一种名正言顺的必然。
其三,处在当下物质化几乎无处不在的整体社会氛围中,我们的一些作者、编辑家们,常常是只顾现实、只重眼前,却很少有人去温习历史、崇敬前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去珍惜他们的创造性成果了。所以,视野里除了歌词,恐怕连戏剧、文学也极少有人顾及、鲜有问津,更不用说去关注戏曲与说唱文学了。自然,将音乐文学与歌词混为一体的现象的屡屡发生,便也就见怪不怪了。
记者:但我还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认为音乐文学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就是您所说的由多个品种构成;另一种是狭义的,就是专指歌词。对此,您本人赞同吗?
晨枫:这一论点我也注意到了,它应当是庄捃华先生在她的《音乐文学概论》专著中提出来的。庄先生主张把音乐文学分为狭义音乐文学、戏剧性音乐文学与说唱性音乐文学三大类,显然,其中的狭义音乐文学就是指歌词。但是,如果从学术理论应有的严谨性与科学性角度出发,我本人对于这种区分方法是不大认可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音乐文学既然是与音乐相关联而生存、并涵盖多种门类艺术形式的艺术品种,其中的歌词就是歌词,或者称它为歌诗或者可唱的诗,它在本质上属于音乐文学范畴,但如前所述,它毕竟并不能包容音乐文学这个概念的全部,比如歌剧、音乐剧与戏曲中的剧词、曲艺中说唱类的唱词等等。我想,庄先生其所以要将歌词定义为狭义的音乐文学,意在让歌词与戏剧性音乐文学、说唱性音乐文学一起并列,但我以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试想,如果依照此理,狭义的音乐文学是指歌词,它可以与戏剧性音乐文学与说唱性音乐文学并列,那么,其中以歌剧、戏曲、音乐剧等等为主的所谓戏剧性音乐文学,又都属于戏剧文学的范畴,而戏剧性音乐文学是否还要从戏剧文学中剥离出来呢?说唱文学与说唱性音乐文学也是一样。再说,我以为如果这样,至少是把发端于宋代、兴盛于元代并绵延至今的我国多种多样、色彩斑斓的戏曲剧词以及从20世纪四十年代起步的我国现代歌剧剧词这一音乐文学瑰宝,从音乐文学中剔除出去了,而这将是何其重大的损失!于此,所谓狭义的音乐文学,表面看来上是纯粹了歌词,实质上却是修正了传统的音乐文学的原本概念,实不可取。
应当承认,当下我们的音乐文学研究工作,还基本上仅仅局限于歌词,但绝不能因此而把本来属于音乐文学范畴的剧词与说唱词剥离给戏剧文学。再说,在事实上,我们有不少的歌词作家们已经涉笔音乐文学的其它门类了,比如,乔羽的儿童剧《果园姐妹》,阎肃的民族歌剧《江姐》、京剧《红灯照》等,王晓岭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刘麟的民族歌剧《木兰诗篇》以及马金星曾经创作的曲艺说唱作品等等,都有力地说明了,歌词作家们在从事歌词创作的同时,兼及戏剧与说唱文学类创作,是十分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而我其所以坚持认为歌词是音乐文学的主要品种而不是全部,既意在让音乐文学回归它原本的内涵,也意在促使我们的歌词作者们在从事歌词创作的同时,能尽力拓宽自己的创作领域,将与音乐有关的文学品种尽可能揽于自己的笔下,从一位歌词作家跃升为一位音乐文学家。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歌词与音乐文学关系的一些认识与理解,仅属一家之言。其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特此求教于诸位同行与朋友们。
记者:今天就谈这些。再次谢谢您接受本次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