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儿八千的“徒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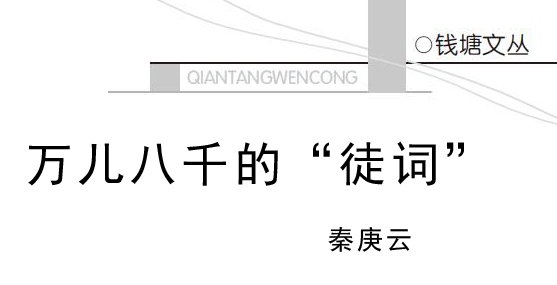
全国各类词刊、词报、词苑上,每年付诸发表的歌词有多少?粗略算来,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万儿八千的歌词被谱成曲发表的有多少?也是粗略算来,顶多一成。又,这些歌词经谱曲经演唱能传播的有多少?微乎其微! 稍为明白的人都知道,凡是能流行的歌曲,其歌词都不是单独发表的,而是与音乐结合后首先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唱出来”,而后纸质传媒刊登,以满足受众的需要。故而,单独在纸质传媒发表的歌词,大多是期待与音乐结合的文本,也可说是“等待戈多”的徒词。
那个作曲的“戈多”就是没来。如今作曲的几乎不读词刊、词报,何缘而来?年青的曲家,他们有自己的创作团队、合作盟友;名声大的曲家,他们忙于完成各类定向约稿,无暇来万儿八千中觅词;还有那些专事为歌手度身定制的曲家,用的是歌手的自选词或自度词…… 于是,各类词刊、词报上的歌词无不是“产能过剩”的景象。写歌词的初衷,就是希望插上音乐的翅膀,现在成了“徒词”,成了“铅字派”词人——假如歌词是父、音乐为母,那徒词就成了“剩男”; 假如歌词是母、音乐为父,那徒词就成了“剩女”,万儿八千的洞房花烛,乃为奢望。
于心不忍,于心不甘!众多的词人开始反思:音乐性不夠,想法设法恶补;文学性不足,勤学苦练专修;创意不行,挖空心思辟蹊径;经营无方,上下左右找“买主”……可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万儿八千的“剩男”还是那“剩男”,“剩女”还是那“剩女”…… 有年轻的词友问及我是否有“徒词”的烦恼?我说“也有,但少有。”长期在专业歌舞团写作,一方面忙于“职务作品”,一方面忙于“社会订货”;再则,我的写作原则是“造船出海”与“借壳上市”相结合;还有,我懂得“不能在歌词这一棵树上吊死”。
昔为“鲜肉”,今为“腊肉”,自始至今,孜孜于词。带着专业的敏感,也带着职业的习惯,我读每一期徒词;带着年代的差异,也带着时尚的潮感,我读每一篇词谈。近期,多次品读两篇歌词文章——
一篇是晨枫为张海宁写的《序言》。他把词作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靠纸质传媒展示其创作成果,并以此产生社会影响的;而另一类,则是凭借自己的作品转化为声音并被歌手演唱后成为歌曲艺术,来跻身音乐领地。”前一类以投寄刊物以词觅曲,“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常常是为迎合某些节日、盛典、纪念会或歌曲征集而创作”,而后一类则是直接同曲作者沟通、合作,“他们的作品多是有感而发,自主意识鲜明,易于富有个性。”他说,“海宁属于后者”,他“真诚祈愿会有更多像海宁一样的歌词作家涌现”!
一篇是许自强评论杨涛歌词的《艺术天平上的舞蹈》。他把杨涛(们)的歌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偏向于音乐性的歌词”,这类歌词有三种情形:①“以豪言壮语吹响时代号角”;②“以山歌俚词抒写民风习俗”;③“以‘花言巧语’装饰时尚风情”。另一类是“偏向于文学性的歌词”,也有三种情形:①“以精雕细描的工笔手法,展示生活写真”;②“以独特的修辞方式,抒写人间真情”;③“以形象隐喻,谱写浪漫遐想”。他对杨涛这样有作为的年轻词作家除了点赞和批评,还指出了前路所在:“不要为歌词只能躺在刊物上面叹息。能谱曲演唱固然是歌词的理想目标,而作为文字稿发表在刊物上,仍能被大众作为一种别样的新诗去欣赏,也有它的艺术价值。”
两位词论大咖,从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作家的不同角度谈到了“徒词现象”“徒词问题”,面对每年这万儿八千的徒词,也引发了我的关联延想——
其一,从诗歌的发展而言——歌谣(无伴奏的歌唱)、歌诗(有伴奏的歌唱)、徒诗(脱离音乐的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歌谣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比如当下流行的那些押韵的、重言复唱的民谣、段子);与歌谣相比,歌诗则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形式、成熟的修辞手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当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就从歌诗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和歌诗都是群体的诗歌、自然的诗歌,而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自觉的诗歌,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得到一种艺无止境的发展。好像有种规律:几乎所有的音乐文学,都会转变为徒诗性质的纯文学。
其二,从晨枫“有感而发,自主意识鲜明,易于富有个性”的希望和许自强 “别样的新诗”的主张而言——徒词应该参考徒诗的发展思路。我只能说参考,不能说照搬。所谓照搬就是脱离音乐,一味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就是“把歌词当诗写”;而参考,就是对音乐不即不离,就是增强文学的自觉性,就是“把新诗作词写”,“把新诗装进歌词的瓶子”。何况当下大多数热衷而熟稔的“徒词写手”,要进入当下歌曲创作的“主笔圈”,或是嵌入当下歌曲工业化的“制作链”,还有“望山跑死马”的路程呢!前些日子,音乐教父李宗盛在“金曲国际论坛”上说:“音乐是一个被低估的行业,人人都觉得他能玩、门槛很低,可是成功的门槛很高。所以比如说艺人,今天这题目叫《艺人的自我经营之道》,但你要先把一个人弄成艺人,才有经营之道,因为你可能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被经营。”由此想来,把徒词写成“个体的词”“自觉的词”,也许是至要的经营之道。
其三,从学习经典、继承传统而言——徒词应该多琢磨一下“乐府诗”。长年来,我们学习古之经典,多于唐宋律绝,而“乐府诗”却有形无形地被疏略了。其实,两汉乐府、曹魏乐府、隋唐乐府、唐后乐府,又特别是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它的语体、语式、语感、语风是可以迅速与当代徒词“接轨”的。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既强调要重视音乐性,又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这不就为徒词写作找到了一个可信又可行的理论之道和经营之道吗?不妨坚持地“拟乐府”吧!
方石出了一本歌集,书名《必须歌唱》,耐人寻味。于精英词家、专职词家之外,徒词作者、草根写手,正执拗地在书写万儿八千,必须歌唱啊!我以为,只要不是伪叙事、伪抒情,那就唱吧!是百灵鸟,就百灵鸟式地唱吧,是猫头鹰,就猫头鹰般地唱吧——徒词……总会有那么一天,万儿八千中的“优”者,会带着“异”的因素,重回歌诗!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