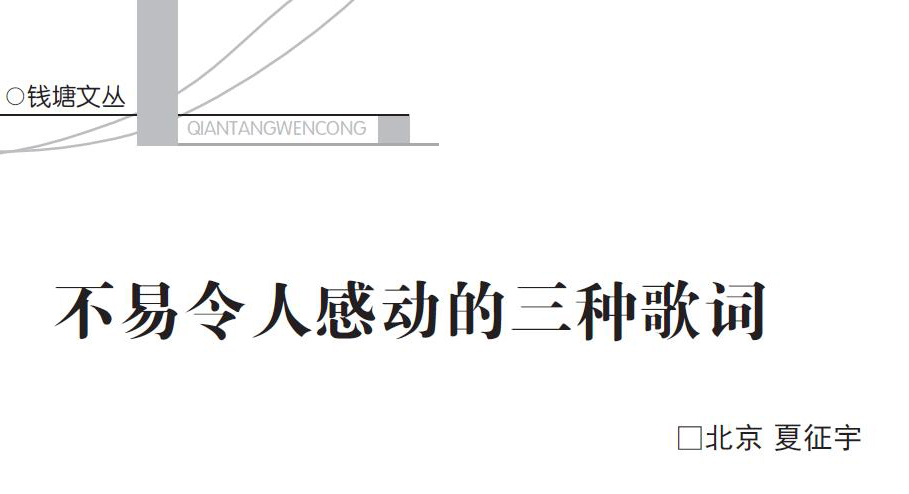村歌好听接地气

2015年底,有两条安吉本地新闻皆事关音乐。一是县女子“竹乐”艺术团,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0周年活动上演出。一是“爱安吉大声唱”总决赛在县体育馆举行。乡土器乐亮相世界艺术之都,民间声乐集体狂欢,不亦乐乎?
有文艺“小资”标榜:每天读首好诗、看幅好画、听首好曲。笔者难改俗人本性,又不懂附庸风雅。与其读当地著名诗人大作、看书画名家“精品”、听网上流行“神曲”,不如读打油诗、看小孩涂鸦、听民歌俚曲。倘下乡采风问俗,则乐不可支。
诉诸听觉的音乐乃艺术中的艺术,较之其它艺术更抽象,也更纯粹。音乐理论家廖尚果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是灵魂的语言,是灵界的一种世界语。”虽然音协在文联下属各协会中的排位,不及作协,但如叔本华所说:“世界在音乐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和表达,音乐在各种艺术中是第一位的。”音乐给人的享受非语言能描述。《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塔外人”木心有夫子自道:“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他有“看在莫扎特的面上,善待这个世界吧”“用音乐来发脾气当然最惬意”等妙语。能谱曲、会弹钢琴的木心,在西方古典音乐上浸淫甚深。音乐涵养对其文学和美术创作,想必多有裨益。刘胡轶为木心名诗《从前慢》谱曲并演唱,可谓一流的“中国好歌曲”。
村上春树业余不仅是长跑狂人,而且是资深的爵士乐发烧友。他有《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一书,还有音乐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其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就取名于欧美某流行音乐。在村上看来,品味一种由音乐和文学语言交融而成的美妙心境,那是具体的影像等有形之物无法替代的。余华也有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叶兆言说他写作时,耳旁一定要有音乐。写小说和听音乐或有隐秘关系存焉。不过,倘一边听曼妙的轻音乐一边写杂文,则有点不对劲,除非边听“红歌”,边写“歌德”派杂文。而我这种连简谱也不识,只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乐盲,作文无音乐之助,难怪文中多有“不和谐”之音。
撇开“高大上”的西方古典音乐,回到乡土音乐上来。1989年编印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安吉系列,虽有歌谣卷,但只收歌词,不录曲谱。王季平和尚忆琴合编的《安吉山歌300首》附20种曲谱,以示山歌原本是音乐文学之属性,只是如今恐怕已很难听到传唱。贝多芬有“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之名言,而民间谣曲颇能寄托乡愁。“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近年来,安吉有的镇村推出弘扬乡土文化的镇歌、村歌,颇可点赞。如孝丰镇的《孝之歌》,“顺着婆婆的手指……把孝字刻在心灵深处。”再如郎村、上舍、长潭的村歌《美畲山》《舞出精彩》《长潭长》等,不乏乡野风韵。村歌创作者多为本县文化干部。以打油诗赞县文广新局黄卫琴等几位才女:“写词谱曲加演唱,三个女人一台戏。村歌好听接地气,乡韵遍传西苕溪。”
古人将“乐”列为“六艺”之一。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 音乐陶冶情操最直接而显著。恩格斯说:“音乐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不过,这“需要有辨别音律的耳朵”(马克思)。故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部分。善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说:“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没有早期音乐教育,干什么事我都会一事无成。”音乐于科学亦有补也。
如今,面向少儿的各种器乐培训,在小县城生意红火。想当年递铺街上,跟县文化馆搞音乐的柯国强先生学过电子琴的,人数加起来估计超过一个加强营。“艺考”能过关固然好,但演奏技艺并非欣赏音乐之必备前提,就像美食家未必会烹饪。学会聆听音乐,无形的节奏、旋律和音色,就会为你呈示出“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改木心一金句:“人头攒动众声喧哗之处不必找我。如欲相见,我在大音稀声处,能做的只是聆听一管洞箫的如泣如诉”……想起徐悲鸿曾以蒋碧薇为模特画吹箫图。凤凰台上忆吹箫,多少事,欲说还休。
有一金姓邻居,虽家境窘迫,但家长勒令年轻子女都要学一种乐器,不知是穷开心,还是瞎折腾。不会任何乐器的我,念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古语,五音不全的我,打算退休后报名参加县老年大学合唱团,发自肺腑地纵情歌唱“伟大的党、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