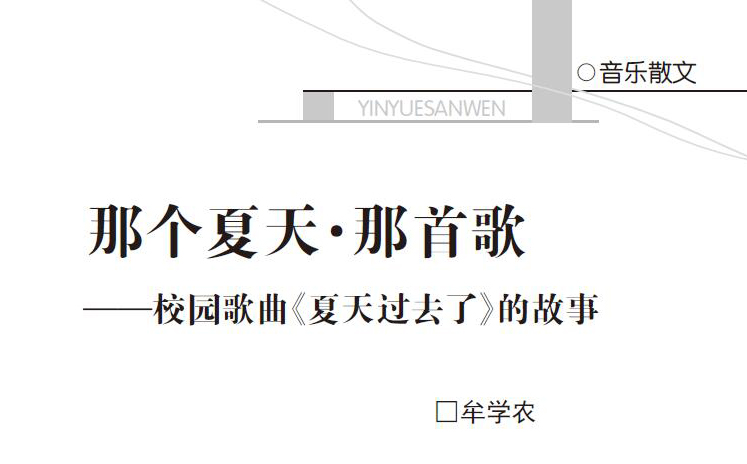歌词的文学性升华

歌词是一种界于文学和音乐的特殊艺术母体,它用于作曲家谱曲成音乐作品。此外,它又可独立与音乐之外的一种文学体裁。有人理解它为“能唱的诗”,似乎这就是歌词的标签。然而纵观我国千余年来的词作,远远没有如此简单的定义可以完全地表现它。
接到《花港》编辑的电话,约我写些有关歌词写作的文章,尤其对浙江歌词创作的个人见解,也可以评说特色、方向等内容。放下电话,我一直在思考,写什么好呢?我也曾在国内外一些音乐院校讲学,写篇把这样的文章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列位有所不知,虽然我也写过一些歌词,但在我的所有讲学活动中从来没有歌词写作这一内容,因为我一直以研究民歌为主的。虽然对民歌的歌词表现手法和技巧有猎涉,但要议论当前我省歌词创作,那真的给我出了难题。
苦思冥想没有出路,于是,读完了《花港》复刊以来的浙江作者的词作。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样边读边作笔记地认真过。从中许多歌词真是只有在细读、重读中发现它们的美,而且感到由衷的折服,甚至有信手谱曲的冲动。但要从里面总结出些什么来,或者由此归纳到某种理性的东西并以文字表达,这又感到很难。看来看去,与以前我省“浙派词”相比,在文学性上有较为明显的不同,那就抓住此题,妄作评论,不知当否还请方家指正。
(一)
说到浙派词的历史,可能许多人还不太了解。在明代后期至清初,浙派词有“东”、“西”两派。在文学风格上东派婉约,西派大气。但在清初时,两派相互影响,都倾向于清丽之美,其中的“柳州词派”就是如此。
柳州词派不是广西的柳州,而是以嘉善城外柳州亭命名的。当年明末的“八子会文柳州”,所谓会之文大多为词作,会文之友大多为词人,他们常相互唱和。此派词人最多时达一百四十多人,作品之多实在令人吃惊!要知道,有词牌的词,在明末大多数已失传了唱腔与曲调。文学家冯梦龙所广为搜集的民歌与词作,也只记录了文字而无曲调可查。因此当年的词作仅是文学作品而已,虽然每首词前都冠有曲牌名,但已都不能以音乐的形态来传播。当时的好词,是因为写词在格律、平仄上的要求比诗更高、更难。
柳州词派许多词人的作品,被收录在各种词选中,影响很大,现在研究柳州词派的学者也很多。同济大学金一平教授所著的《柳州词派》一书中说:“柳州词派拥有自己的词人群体,在当时词坛上,与云间、西陵、梅里等词派相颉颃,对明清之际的词风递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入清后,“词作多田园词和归隐词,词风也更加清丽。”可见“清丽”早就成为浙派词的传统风格了。在词失去它的音乐功能之后,在文学性方面有了新的面貌。当然,词人都是浙人,词作也多写浙江的人文题材。词人钱丹《忆江南》有道:“江南忆,最忆是乘船。泊到长桥萦柳线,眠将短笛撩萍钱,月上未知旋。”钱荣的《临江仙•和墨仙园居》更有田园之韵:“桐院深深秋影满,奚囊偶寄禅龛。邻园修竹倚墙南。青莲新粉落,叶叶喻华严。”像这样清丽之风的词作,几乎十分寻常,在《柳州词选》中举不胜举。
“燕儿南飞,衔相思红豆,欲说还休,小楼月如钩。”(钱丹(明)《江南秋》)
“泊到长桥萦柳线,眠将短笛撩萍钱”描绘了词人坐船过长桥穿柳云,以柳丝系船挂船,用手中的短笛在似醒非醒中撩拨河水,撩拨水中的小浮萍。这是我浙水乡最美丽的情景,画面感顿时显在眼前。我们所说的文学性,就是在作品中以文学的手法来达到非凡的感染力。其要素有“生动、深邃、空灵”三个方面与三种境界。
所谓“生动”,即述有所物,有形有像,色彩鲜明。“生气而有动感。”这是词作较为容易达到的境界,也是作品最起码的内容和实质,是咏之有物的“物”。上述钱梅之句,就是例证。“萦”和“撩”的动作增加了画面动感,一个活生生的实境。这在我们当代浙人词作中也常见:
“船娘入画墨未干,卷起红袖羞得山水暗。”(念灿华《船娘》)
“啊,江南花雨,滴滴答答,一声声优雅,唤醒梦中的琵琶。啊,江南花雨,飘飘洒洒,一缕缕芬芳,香染岁月的佳话。”(徐福清《江南花雨》)
“南浦莺啼,一痕沙外桃花水。江城芳草系裙腰。人醉春风里,却好时光多丽。一半儿,红晴绿意。少年游沿,倚醉随鞭,一丛好花气。”(柯煜《烛影摇红•集词目成篇》)
这些词句所描绘的情景,有声有色,有静有动,一脉传承了浙派词人的传统风格。在浙人眼里的浙江,对美的感悟以及表达,是传承有序的。请看古今词句中的韵律和节奏,也是十分相似,只是在押韵上,韵脚与词意的结合上,当代的词作稍为硬一些。
(二)
词作的意境之二,应为深刻的内涵,而这种内涵包括主题之外的延伸寓意,而不是故弄玄虚的“玩深沉”。这种寓意的延伸应该是愉快的、轻盈的、随意的。
“砚点飞花,檐沾弱絮,炉烟小溪湘帘暮。春风不解动人情,人情怕送春归去。”(李标(明)《踏莎行•春闺》)
古代浙派词在二度音乐创作的功能上逐渐淡化,因此,词的诗意更浓,情意更深了。歌唱的可能性弱了,但在吟诵或朗诵时,依然有顿挫抑扬,声情并蓄之感。词人们相聚会时,一个个自吟佳作,或眉飞色舞,或慷慨激越,借景抒情,为浙山浙水着色添彩。在他们的词中可闻其声,可睹其音容笑貌:“钱塘江上,雷轰电裂。雪山一片茫茫。鲛叟扬绡,冯夷击鼓,数车白马成行。……”(魏学渠(明)《望海潮•中秋后三日观钱塘潮》)
词中气度非凡,鲛叟和冯夷都是水神。作者借钱塘潮之气势,抒胸中之志。又有:
“已远喧阗,渐觉幽凉,无过西泠。政微霜欲下,满船风叶。枯荷未尽,几点残萤。……”(钱继章(明)《沁园春》)
词中所述远离红尘,独自忧伤,“枯荷残萤”,一派孤凄,读来十分伤感,如见愁容孱身。
当代浙人写浙江的词中,溶入了社会大背景,丢弃了那种凄美伤感,即使有愁情也轻盈流畅:
“一对新燕/飞回旧时花窗/翩翩少年/转身鬓发染霜/几许相思/停泊杨柳岸旁/箫声暗哑/多少泪流成行/乌篷船轻轻摇晃/摇散了水中月亮/淡淡的忧伤/美丽的过往/那一曲丝竹里谁将老歌吟唱?”(阡寒《江南丝竹》)平平淡淡的古老的江南丝竹,在词人耳中化成了新燕老窗,化成了白发如霜,心绪化作声声轻叹,人生,就如同流水轻淌。无形的隐喻,藏得很深,很巧,这不就是深邃么?
今日写钱江潮的词很多,杭州词人施翔的一首《钱江潮之恋》却写出了爱的转意:“浪花开/潮头白/你的爱坦荡不容猜/去无声/来又快/你总是让追梦的人很豪迈/涛声在/不徘徊/我的爱执着不更改/再寂寞/再无奈/对你的思念总是与生俱来。”古今写钱江潮的不知有多少,而借潮来说爱的,却是独此一家吧!这就是今人更胜古人一筹呀!
(三)
词作的意境之三,为“空灵”。空灵不是空洞,空洞的原意为只剩外框,内无实质,作“皮壳”之解也。空灵也不是空虚,虚者,假也。而空灵是指内容、实质太丰富了,只有用若即若离的手法来增加其内涵的一种状态。这若即若离、有影无形、似又不似,但内在又是深刻维系着的一种叙述形态,更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其实,空灵是空幻加灵动,是一种文字的表意手段。
在古代的诗词或文章里,空灵的手法也常见:“……把钓竿暂憩夕阳西,觉蝇情云影排空际,觑蜗名,梦间儿戏。……”(孙煌清《哨遍》)还如清代计能的《点绛唇•题画》中有“自在幽闲,久与风尘隔。谁与识,个中萧瑟。未许忙人得。”句,像写自己,又像写他人,前后句意境的跳跃,常是古人们从自己到社会,从个体到自然山河、到他人不同景象的描绘,只有深知其写作背景,才能知其用心。
在当代,由于受较前卫的模糊美学的影响,这种空灵的现象实在太多了,多得有点滥。但是,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空灵却是一种极高且美的境界,不是一般功力所能达的。众所周知的《涛声依旧》是从《枫桥夜泊》演化过来的。“今天的你我怎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怎能登上你的客船……”那种回不去的回首,那种流水东去的无奈,刻画得太入木。
“我驾着云/穿过你三世缤纷的传奇/我忘了自己/汇入你的菩提无色无意/原来我一直在这里/在你的光里……”这是王迎的《禅醒》。禅,本来是一种精神,本来就很空灵。整首词里没有一个佛字,但含却了很深的佛道在其中。
纵观当代浙词,追求词的深邃和空灵已成为一种倾向,似乎没有达到这一点就算不了“高”。笔者特别欣赏王迎的词,在空灵的境界里还有一丝似乎的哲理,很令人回味。她的《刹那永恒》便属此类:“……一刹那/两相认/这样的真/待我仔细看/你的笑容已无痕/我的永恒也许只是你的刹那/你的每个刹那,都是我的永恒……”爱有刹那,爱也有永恒,两者的复杂交错,但又非常辩证。这就是文学性得到了升华。但是也有许多刻意追求空灵的,往往反而会滑向空虚了。片面的、故意的空灵化,就会变成朦胧诗,失去了歌唱性,让作曲家们摸不着头脑,很难去捕捉音乐形象,这也是一种极端。
在书写此文时,笔者翻出2008年出版的“浙江百家词选”一书,对照近年来的《花港》新词,总体感觉在歌词的文学性上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文学性升华,使词作的思想容量大大地增加,可以延伸出许多遐想。笔者的《春天•秋天•我梦你中》有这样几句:“我们的梦看见同一个美丽/因为/我们的心只隔着一朵花的距离。”这也是一首“爱与梦”的歌,却从“我们”的投情去表达,让人浮想。当然,生动、深刻、空灵在一首词里不能绝然分割。一首好词谱成歌,会流传,会长传。
最后,不得不说说在注重词作的文学性的同时,不可忽略了它的音乐本质。如果只是一件好的文学作品而不能谱曲成歌,那也只能是“半成品”而已。“半成品”实在太多了,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顿悟!建议词人也学点音乐,最好会唱歌。因为只有歌者才能真正体会到词曲结合最佳效果。浙江是一个出词人的地方,《花港》是块百花园,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