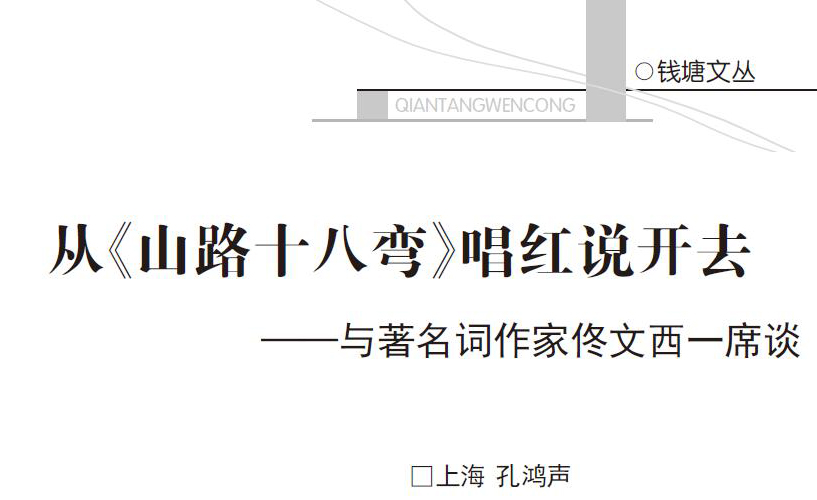不善为诗难为词

一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至今还有人视诗与歌词如同水火,好象歌词一旦有诗的渗透,就会降格,甚至变质,而他们却又堂而皇之地美称歌词 为音乐文学!
既是文学,又怎能离得了诗呢?
殊不知,“一切纯文学都应具备诗的本质”(朱光潜),“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艾青),“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入场券”(余光中)。诗之于文学,是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色彩,一种韵味,装点着、成就着文学艺术作品的纯度与高度。把诗当作歌词的异端而歼灭之,就是不追求纯度和高度,甘愿让歌词沦为劣等品。
二
对于“歌词是为音乐服务的“提法,我既蔑视,又反感,怎么能把一歌之主的歌词,降到“服务”的地位呢?离开好的歌词(一般先音乐而产生)何来好的音乐呢?
正确的定义,是余光中的八个字“诗与音乐结婚,歌乃生。”是“结婚”不是“服务”,两者互相从属、互相补充、互相美化、互相完善。
三
歌词,只有经过谱曲和演唱,见之于声的时候,才是所谓“时间艺术”和“听觉艺术”,未谱曲的歌词,就是歌词,是供作曲家眼睛审视和心灵感应的一些“话”。作曲家着力从“话”中追寻的是什么?一是抒情氛围,二是文学意味,而这正是诗才充分具备的。说穿了,作曲家要求歌词提供的,无非是诗味,因为诗味才是引生乐思和旋律和根由。
请不要拿“时间艺术”和“听觉艺术”作拒绝诗艺渗透的借口了!
四
诗,是语言的艺术,因为用得是艺术 语言。所谓艺术语言,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艺术处理的语言,已不是生活语言,也不是散文语言、小说语言,更不是标语口号式的语言,而是比这美丽得多、高雅得多、精致得多、深刻得多的语言,因此,是特殊语言、技巧语言和纯粹语言。
语言就是诗的本身,写诗就是写语言。语言的劣手,不可能成为诗的高手。
就语言而论,歌词与诗,是同性格的。作为一个有见地和抱负的歌词作者,在语言问题上,应有高度的觉悟和高超的才能,而这,只能从诗艺中求得。
五
歌词,不但应该是文学,而且应该是美文学,美得跟诗一样。其美之一,是意境美。意,是作者要抒发的情思,它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是不具体的,因此是不可感知的(感觉器官感觉不到)因此是不生动的,因此是非文学的。所以,意,得借境来表现。境,是手段、是形,是象,是物。任何物,总是具体的,因此是可感知的,因此是生动的,因此是文学的意与境的关系,就是灵与肉的关系,魂和体的关系。有灵无肉成魂不附休,即使思想再伟大,口号再响亮,也与文学无缘。而这样歌词,是太多太多了。
不善于创造意境美,想写出高品格的歌词,难啊!
六
诗美中,还有个空灵美。即不着重于实写(纪录生活的面貌,提供可看的),而着重于虚写(提炼情思,提供可想的),风虚写所创造妙景、妙意和妙趣,都是空灵美的闪光。一味实写,只能使作品挂上“死板”“无味”的标记。
歌词,能没有空灵美吗?
诚然,没有空灵美的歌词是有的,但,只够得上是“大实话”、“快板”或“押韵的句子”。那是文学之外的另一类东西!谁让他把诗看成歌词的祸水呢?
七
好的歌词,就是诗。有传得很开的歌曲的词为证。
古典型:《秋水伊人》、《送别》(电影《城志旧事》主题歌)、《笼儿不是鸟的家》(电影《杜十娘》插曲)等。
民歌型:《牧羊曲》(电影《少林寺》插曲)、《回娘家》等。
古典民歌结合型:《知音》、《莫愁,莫愁》等。
新诗型:《我的祖国》、《望星空》、《血染的风采》等。
以上歌曲的词,因为本质上具备诗美,故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故没有变成曲的附庸。
八
哲学家贵在他的眼力与深度,诗人贵在他的激情与灵气,两者结合是全方位的成熟。
眼力+深度+激情+灵气,难道不也是一个歌词作家所需要的?
我以为:在歌词的周围高筑篱墙,不准哲学和诗进入,这是当今“词多好的少”的主要原因。
(一九八八年八月五日,长沙,蝉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