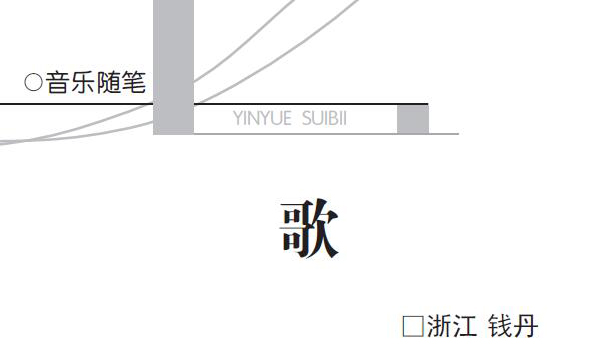歌词的内功

歌词的发现
歌词下笔之前,最重要的是“发现”两个字。发现什么?
首先,是要发现“歌唱性的题材”。不是所有的题材都适合歌唱,这一点是要特别指出的。有些题材适合写成新闻故事、写成时评漫议、写成表态文章、写成诵读文字……你楞是要把它写成歌词,多半是吃力不讨好,让你力不从心、左右为难,让你捉襟见肘、游戏文字,直到让你遭之所讥、所笑、所嗤。
其次,是要发现“歌唱性的角度”。可歌可唱的题材,需要可歌可唱的角度。凡歌唱性的题材,苏辛柳永们早已写完。后人之所以还在继续写词,是因为一切可歌唱的题材之新角度,正期待着后人崭新的发现。无角度的写作不仅笨拙、矫情,甚至很滑稽、很虚妄。后人的任务,就是去探求另一条新的创作思路,去发现另一个新的构思角度。
要发现“歌唱性的风格”。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角度,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表现风格。风格即色彩,风格是对题材、角度形象化、性格化的表现。古典风、民歌风、唱词风、新诗风、散文风……风格体现在语言,关涉语境、语感、语风、语体等等。词人应该用不同的彩笔来“画”不同的歌词。
我们应该——
像荒野的求生者那样,去搜寻裹腹的可食之物——发现“歌唱性的题材”。
像战地的狙击手那样,去确定射击的最佳位置——发现“歌唱性的角度”。
像T台的模特儿那样,去潇洒夺睛的翩翩英姿——发现“歌唱性的风格”。
歌词的角色
歌词,是歌唱的韵词。歌词与诗歌有很多的相似点,也有很多的不同点。不同点最根本的是歌词姓“歌”,而诗歌姓“诗”。歌词是供给演唱的文本,而诗歌是供给阅读的文本。所以,有人把歌词叫作“歌诗”,把新诗叫作“诗歌”——原来,诗歌是文字,而歌诗是语言,微妙其哉!
从这个歌唱的前提出发,可以发现:诗歌写作多半只有一个主人公,即“抒情主人公”;而歌词写作却有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抒情主人公”,另一个叫“歌唱主人公”。歌词作者心里想说的话,并非自己“主人公”一番就能了事,还得借助“歌唱主人公”来演唱才能奏效。
演唱,就是“演歌”,是表演艺术。表演一定离不开“角色”。曲艺是“说法中现身”,而戏剧是“现身中说法”。不管哪一种表演(现身),都有鲜明的角色身份。无角色的歌唱,即没有“歌唱主人公”的歌唱,是泛泛而唱。究其因,乃是歌词在泛泛而写。
有人说:电视剧的插曲那么受欢迎,歌者并没有角色的“现身”呀!其实,歌者是剧中人物的代言人,亦或是观众的代言人,角色在此中,角色的情感在此里。词人所言事,是代角色说事,词人所言情,乃代角色表情。词人的任务就是用自身的观照去代角色言情说事,不懂这一点,就不懂词人自己本该是什么角色。
不妨从几首歌去思考一下歌唱的“角色”(歌唱主人公):
晓光的《那就是我》——“我”是什么角色?
车行的《常回家看看》——“谁”应该常回家看看?
郑南的《请到天涯海角来》——“何人”请你去天涯海角?
歌词的逻辑
凡词,写作都须有由头。无由头写作,容易变成无厘头写作。有由头,即是有缘由、有体会、因事而发、缘情而歌。
歌词以抒情见长。抒情歌词往往须有一个抒情的背景,这个背景往往蕴藏着故事,这故事或是一个极简的情景、一个极简的情节,甚或是一个极简的细节。这个故事、背景,是心藏之事、胸怀之景,是不必要刻意说出来的;而这些情景和细节,却是要着意流露出来的,它是眼前之物、易感之景。
因此,写歌词必须讲究逻辑,讲究叙事的逻辑和抒情的逻辑。
叙事逻辑,就是通常说的“前因后果”——可以归结为:把“怎么样”都交代得合理而又清晰。要讲究叙事的因果由来,那种突兀而来的说道,会让人一头雾水。凡逻辑性强的歌词,会从歌词的起始段中显现,谓之“铺垫”
抒情逻辑,就是通常说的“情感共鸣”——它是情感起承转合的动力,通过心灵共鸣,传递给受众。讲究抒情的逻辑性,是让人去感受,而不是去猜度,须把“为什么”交待得融情入理,让人油然生感。凡不讲究抒情逻辑的歌词,定然让人感到生硬、勉强、莫名。
叙事和抒情讲究逻辑,有几首“叙咏词”值得我们琢磨:
乔羽悠然道来的《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阎肃毅然道来的《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张藜率然道来的《篱笆墙的影子》——“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歌词的语法
1980年代初,“庐山词会”,听晓光说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一些趣事。他说有好几个文学教授给他这首歌词提意见,说:歌词也得讲究语法,讲究主谓定状宾补呀,这歌名是语法不通,应该叫《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才对!据说,后来这个“文字官司”煞有介事地打到最著名的语言学家某老先生那儿去了。面对这些个教授,某老先生会怎么裁断呢?晓光道,后来听别人跟我说的,某老先生笑眯眯慢悠悠地说:“嗨!不要去跟诗人词家讨论语法的问题嘛!”
的确,歌词的语法与文章的语法有些大不同:为了简短,可以删去前定后补;为了情感,可以灵变词性词义;为了节奏,理应重组句式语式;为了歌唱,理应多用俚词口语……不熟悉古典诗词和民歌民谣的人,自然会提出一些个缺乏诗词常识的问题,相互交流自然就对不上频道。
1993年,苏芮唱的《牵手》在大陆一举创下150多万张的销量,成为当年唯一能与张学友《吻别》相抗衡的作品——“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后,在《广播电视节目报》上读到某部长先生的一篇文章,以端正文风的名义,批评李子恒词曲的《牵手》语法不通。没有人反驳……2011年,河北怀来“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征歌,我写的《为了新中国》荣登榜首。歌中唱道:“喊着你的呐喊,唱着你的绝唱:为了新中国!想着你的理想,念着你的信念:为了新中国!”——这算是实践的“回应”吧。
歌词语法的出新,就是让习惯了常规语法句式的人读了不舒服、不习惯——这就对了。颠倒语序、灵变语义、改装句式、紧缩字句等等,是词家语法的常态。当然,出新了的句式也不能生搬硬套。2016年,有一首写“初心”的词,不仅套用《牵手》的句式,还把“幸福着你的幸福”顺手牵羊进来,不仅不出新,还明显“袭”了。
歌词的修辞
歌词是美文学,歌词的语言是沙里淘金的语言。一切皆在其中——语言,是歌词艺术的第一要素,语言功夫是词家的首要功夫。要把词意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认认真真学习逻辑和语法。学了逻辑,语言才条理严谨;学了语法,语言才明了通顺。但要写好歌词,还必须扎扎实实地学习修辞。
修辞,就是修饰、调整语言。修辞的目的,是在讲究逻辑、语法的前提下,炼篇、炼句、炼字,让歌词的语言更加形象生动、新颖别致、精警凝炼,更有韵味、趣味和意味。这样,歌词才能让曲家、歌手和更多的听众易感、易知、易思,进而乐感、乐知、乐思——不让人“易”,也不让人“乐”的歌词,是没有出路的。
修辞,就是“换一种说法”:“红杏枝头春意浓”,不如说“红杏枝头春意闹”;“晴天响雷真是响,大海震荡翻波浪”,不如说“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千里万里冰封,千里万里雪飘”,不如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后背顶上了一支驳壳枪”,不如说“后背顶上了一个硬梆梆”……
一般人只知道比喻、比拟、夸张、对仗、排比等10多种常用手法,不清楚现代修辞格有63大类、78小类,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只知道单一使用某个修辞格,不懂得使用复合修辞法;只知道修辞手法仅是修饰调整语辞,不明白对于词人而言,修辞手法却是最常用的写作方法——词人,不能仅做“知道分子”。
歌词字斟句酌得怎样才算好呢?读过的许多诗话、词话中,最数明代谢榛,他可是讲得特别的修辞——《四溟诗话》卷一曰:“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