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令人感动的三种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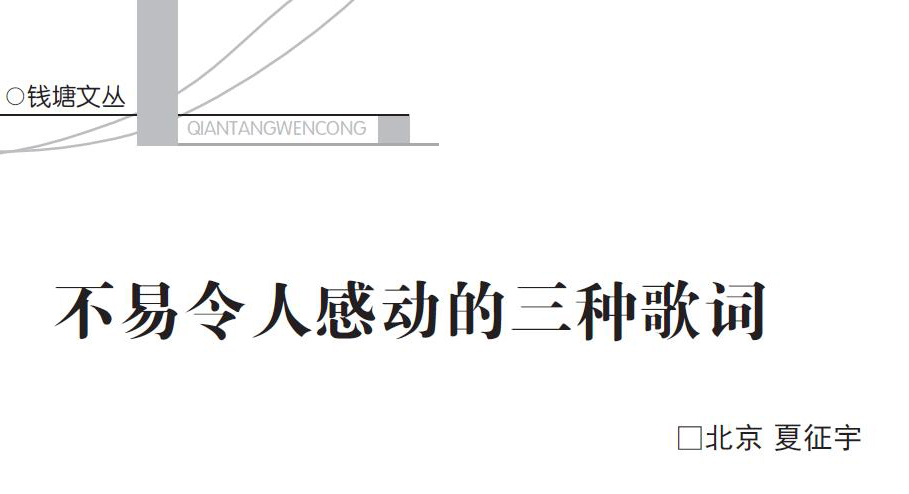
有位词友为当前大量的歌词作品缺乏真诚而深感忧虑,她在来信中问我:“您认为什么样的歌词不能让您感动?”她这看似简单的一问,还真把我问失了眠,因为此前我还真没“反向”地琢磨过这件事。不错,歌词理应感人,我也曾读过听过很多令我终生难忘的感人佳作,但是,不能让人感动的歌词是哪些?又在哪里? 随手翻翻刊物听听CD,再看看音乐电视和网络上那些所谓原创的千奇百怪的歌曲,我突然发现:它们简直是俯拾即是,无所不在!于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许还真有点普遍意义,便索性披衣伏案,按自己的阅读体验尝试着归纳了一番:
第一种叫做:内容过于“抽象”的歌词。这类作品往往是气势压人却又空洞干瘪,张口就是地球如何如何,提笔就是中国怎样怎样,好像不追求宏大的叙事,就不足以体现作者的广阔胸怀。坦白地说,我以前也曾尝试过此种套路,但效果之差实在令我汗颜,所以只好知难而退。或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能力与境界。贝多芬的《欢乐颂》可谓宏大,但它的词作者席勒不仅是大诗人,大剧作家,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因而他站在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宏观世界讴歌人类大同,就显得驾轻就熟,顺理成章。而我们某些词作者明明偏居一隅,多少年都难得出趟远门,却非要去写异国他乡五洲风云,没有切实的素材和感受,就只好效仿别人的笔法,再胡乱添上些这峰那海之类的地理概念来充数,实质上这正是作者生活底子不深,拿着大话吓人的表现。例如前段时间的“澳门征歌”,恕我直言,即使是某些获了奖的歌词,读起来也只像是一份“旅游简介”,基本就没能触及到征歌的主旨。好在最终的一等奖还是给了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这既让我等松了口气,也让我等叹了口气:闻老这首诗写于1925年,整整八十年了,还是没人能超越他老人家——写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作品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别说去感动别人,连自己都未必能感动。
还有另一种更可气的“抽象派”作品,居然将“朦胧诗”的写法,搬进了只能靠耳朵在瞬间聆听的歌词(曲)之中,小滋小味小情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关联地拼凑到一起,自以为得意,却也只能是自己在那里“得意”,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听懂他到底在说唱些什么。这一类作品最常见于所谓的“爱情”歌曲中,又以港台作品居多,这些个作者大概忘记了歌曲的终极目的,还是要给大多数人听的,其艺术价值也是要经过时间来检验的。而你自己的吃喝拉撒,初恋失恋那点儿屁事儿,又与别人,与艺术有何相干? 内容抽象行文冷静的歌词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眼下颇令某些人引以为荣的所谓“政论体”歌词:“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政策性理论性极强的政治概念,通统可以直接填入词中。我一直认为,任何艺术门类都有其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拿来歌唱的。歌词(曲)的特长是抒情而不是辨理,非要生硬地为其涂上政治色彩,非要去跟“社论”,“文件”,“纪要”等特定宣传载体争抢地盘,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且不说你能否仅用百十来字,就把党中央的精神说清说透,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能将所有关键词都合辙押韵地排列组合为一体,也依然无法令我有丝毫感动,因为这样的歌词已毫无诗意可言,只能令人痛苦地联想起“文革”时期的那些“语录”歌曲。
诚然,叙事宏大的作品从不乏精典之作,例如《黄河颂》,《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等,但认真分析这些成功佳作后就会发现:它们绝不只是政策口号的简单堆砌,而依然遵循着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有鲜活的形象,有高远的意境,有澎湃的激情,因而也才能为听众们带来巨大的感动。
第二种叫做:品质过于“粗糙”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歌词界真正具有创作实力的前辈大师和著名作者,没有一位是以作品数量来取胜的。除去其肩负的社会活动,责任,以及年龄精力等客观因素,使他们在作品发表的数量上过于“吝啬”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而我们某些词友,却总也改不掉“广种薄收”的“小农意识”,一晚上就恨不得写出七首八首的,如此的“粗放式经营”只适用于地多人少的原始农业耕作,且只能种些“土豆”,“高粱”等无需过多养护的“粗粮”,“粗粮”就难免“粗糙”。歌词也同样如此,再有天赋的词人灵感也不可能源源不断,没灵感时也要“霸王硬上弓”,其作品质量就必然难以保证。不少老一辈词家对当前歌词作品的粗制滥造现象甚为不满,他们对这类作品的评价是:“多而浅,平而淡,缺乏感性,缺乏深入探索,缺乏精雕细刻,缺乏艺术魅力,无法打动人”——可谓一针见血!想想看,假如我们把这五个“缺乏”,都能一一补足的话,一晚上还能写出几首歌词来?依我看一年能写出一首合乎这个标准的作品就相当不错了!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香港的多产词人林夕一年的最高产量是三百八十多首,平均每天超过一首。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个数字里面有大量的是“友情之作”,是推也推不掉的“苦差事”,我估计我们的词作者中,敢于,能够,甚至早已打破了他这份记录的大有人在。区别在于。人家林老师每首都有钱赚,而我们的高产冠军恐怕也只能是“浪得虚名”了。所以说,我们没任何必要去自己折磨自己,更不该拿这样的“粗粮”,去折磨别人的胃口。
另外还有些作者总不太喜欢用比较规范的汉语书面语言来写作,而喜欢直接套用大量的日常生活俚语,(这方面也以现在流行歌曲中的大部分情歌最为典型)或特别热衷于采用只在某些局部范围流通的方言土语来写歌。他们大概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的作品生动起来,其实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在特定的歌词作品中适当使用某些方言土语和感叹词句,有时确能强化作品的艺术效果,例如《青藏高原》中的那句“呀拉索”,和《乌苏里船歌》中的“啊啦赫尼娜”就对全曲音乐意境的烘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作者所采用的方言土语也都是要经过加工,提炼和筛选,而非全盘照搬的。倘若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的作者都由着性子只按各自五花八门的口音和方言去写歌,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谁也不顾谁,那只会造成表达上的极度混乱,进而形成歌曲艺术创作的一场灾难。
有一位我所敬佩的作者,他的许多作品都颇具水准,但有一首歌唱东北笑星的歌词,就让我犯了难,其中有三句是这样写的:“笑岔了气儿的俏皮话儿/乐出泪的嘎咕词儿/艮揪揪的东北味儿征服了地球人儿”,第一句我还能明白,可第二句中的“嘎咕词儿”和第三句的“艮揪揪”,我就不知所云了。连我这个离东北还不算太远的“华北人”都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又凭什么断定,这样的“东北味儿”就能征服地球人了呢?同样是东北的著名词作家邬大为先生,假如他也怀着对当地方言的执著偏爱,将电影插曲《红星歌》中的歌词:“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写成“红星闪闪贼老亮,红星灿灿贼老热乎……”那这首歌还能听吗?还能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吗? 所以说,日常口语和方言俗语可以用,但应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写出来的歌词连基本意思都令人费解,又怎么能让人感动呢?其实,标准汉语本身,已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营养,足以表达任何复杂的情感,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理应对其保持充分的尊敬。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去大力推广各自的家乡方言,既然你的歌词要在全国范围发表或演唱,那么你就应该尽量使用标准的,规范的,能够通行全国的语言。
第三种叫做:情感过于“勉强”的歌词。也许是历史的原因和歌词强调“大我”的特点所导致,这种现象在写词的人中颇为普遍,而写诗的人则要相对好些。歌词必然要寄托作者的情感,但情感这东西又很微妙和复杂。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有时发自肺腑,有时也会言不由衷。对歌者而言,谁又敢保证自己的每一次抒情,都是完全真诚的呢?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大多数人的情感,所以也才会有这么多众口一词情感勉强的泛泛之作。
但也不能由此就断定我们的歌词为“虚假”,因为“虚假”一般是指:你明明巴不得永不还乡,却偏要违心地说自己的家乡赛过天堂;你明明很讨厌鄙视你的顶头上司,却偏要称颂他的英明和伟大。类似这样完全违背作者主观意愿的虚假之作,曾在封建社会的皇宫里大行其道,那只是由于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所导致,而现在已不会再有谁逼着你去歌功颂德或是义愤填膺,所以我们更没必要去写那些言不由衷的歌词了。
我所说的情感过于勉强,是指作者对于自己所要咏唱的对象,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观察体验,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感悟。例如让很多人反胃的那句:“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网络歌词,其实我至少在七八年前的某一天就曾听到过这句”名言,那是在一次酒后,朋友们拉着我去某家歌厅“K”歌,在那里发现了一伙刚吃过“摇头丸”的非常男女,他们一边兴奋地“摇头摆尾”,一边还齐声朗诵着自己瞎编的顺口溜,其中除了这句著名的“鼠语”之外,还有什么:“命苦不要怪政府,没钱不能赖社会”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胡话。真没想到事过多年后,用这么一句狗屁不通的烂词作为高潮段的所谓情歌,还居然会有人为它的”著作权“打上了官司。
话扯得有点远,我是想说明这首歌曲的“原创者”,显然对于爱情的理解过于异化,至少也是体验不深。像这样并不懂得爱情却还硬要去歌唱爱情的,就是“勉强”。老鼠所爱的又何止是大米?好像就没有它不爱的东西!拿老鼠的偷食来比喻爱情,难道还不够“勉强”吗?谁要是能被这样的“爱情”所感动,那他自己恐怕也快要沦为“硕鼠”一族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要想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要想让我们的歌词能给人哪怕是稍许的感动,就应当去选取那些首先能让自己感动的事物做题材,然后再用晓畅易懂但又绝不粗俗的文学语言,将自己的最真实情感完美地表达出来。




